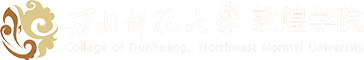2017年迎新典礼致辞
敦煌学院院长 田卫戈
2017年9月12日 敦煌

敦煌学院院长 田卫戈
2017年9月12日 敦煌

各位领导、嘉宾朋友、各位老师、同学们:
今天,又是一个欢喜的日子!我们正式迎来了敦煌学院2017级105名新同学。首先,我代表西北师范大学敦煌学院全体师生向新同学的到来表示热烈的欢迎和祝贺!
今年105名新同学有男生40人,女生65人。少数民族中有2名藏族同学,也有从山西、山东招收的10 名学生,省内的学生来自兰州、平凉、定西、庆阳、武威、陇南、张掖、甘南、以及酒泉、嘉峪关等地市,敦煌本地学生1名。现在,敦煌学院共有448名同学在学院就读。
105名新同学的加盟,标志着敦煌学院顺利完成了前后四届学生的招生任务,学院本科教学建制有了一个圆满的结果。
2014年6月28日,敦煌学院挂牌成立,2014年9月教师节的时候,我院为首届大学生举行了开学典礼。现在,敦煌学院已进入办学的第四个年头。当然,对于每年的新同学来说,重要的不是学院在哪里,而是敦煌在哪里,当你选择“敦煌就读”时,最大的疑虑或最大的期盼,我想就是“敦煌”这两个字。
因此,我也要从“敦煌”说起。敦煌,是丝绸之路的重镇,历史文化名城。这里有无数的传说,尘封千年的壁画,还有神奇的鸣沙月泉……。最重要的是,这里吸引了一批又一批朝圣者,敦煌被称为朝圣者的敦煌。一代代朝圣者续写了敦煌的历史,一代代朝圣者也让敦煌走向了世界。这些朝圣者以坚定的、宗教徒般的步伐,经过几年、半年,或三个月时间,到达这个流沙中的绿洲。历史告诉我们:在规模化的朝圣之前,西北有过令人痛心的经历。从19世纪中叶以后,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使得清政府开始允许外国人进入中国内地。一大批外国“探险者”开始涌入,英国人、法国人、俄国人都进入了中国新疆,掠走了大量文物,尤其是瑞典人斯文•赫定从1890年开始三次考察,发现了著名的楼兰古城。最后,在我们主动出击下,他资助的“西北科学考察团”历时八年发现了居延汉简、准噶尔盆地、恐龙化石、高昌遗址以及其它自然科学方面的成果。
也因此,在藏经洞被发现以后,西方人可以轻车熟路、轻而易举地取道敦煌来掠夺文物,中国西北的文化价值在敦煌藏经洞被发现之前,就已经赤裸裸地暴露在别人的眼皮下。斯坦因、伯希和等人掠走的敦煌写经,迅速在西方学界引起了巨大影响,由此诞生了“敦煌学”这门国际显学。直到1930年前后,中国政府以教育部长蔡元培为首的“古物保护委员会”成立,才真正有效的阻止盗宝者的所谓“探险”。在此之后,从官方到民间,从文化学者到艺术家,开始了自己的“朝圣之旅”,引发了“本土西行”这样一个历史事件。
从今天来看,“本土西行”的作用和功效并不亚于去异域求学的“海外西行”。 我不知道同学们是怎样来敦煌的,但绝不会步行而来。但是在当时,偏远的西北交通条件非常艰苦,去西北需要有一定的胆识、方法和毅力,比如,他们多是搭乘当时被称为“羊毛车”的二手苏联大卡车从兰州出发或找机会蹭车,比如吴作人搭乘李约瑟的车子从酒泉去敦煌,韩乐然是搭乘路易·艾黎的捐赠车西行,很多地方是坐马车、毛驴车、牛车、载货车、工程验收车甚至步行。他们想尽各种办法,走向西北,绝不退缩。李丁陇约带领13名学生沿玄奘之路西行,中途12名学生放弃,只有一个敦煌的学生叫刘方跟随他,他后来在兰州、西安、上海、成都、重庆等地举办敦煌“敦煌壁画临摹展”,引起人们对敦煌的关注,他的行动引发了张大千以及常书鸿、韩乐然等一批艺术家的西行。张大千与儿子张心智,女婿萧建初以及孙宗慰等从成都经兰州至敦煌,在敦煌莫高窟、榆林窟临摹200余件壁画,张大千说:如果不是喜欢,来了也会走!他一待就是两年多,舍不得走。孙宗慰经过重庆、成都、西安、兰州沿河西走廊写生,创作有油画、水彩、国画、速写等。王子云1940年率民国政府教育部“西北艺术文物考察团”一行沿途考察,所谓“一行”,最后到达莫高窟的实际只有两、三人,就是王子云、雷震、邹道云,人虽少,但临摹不小,有长6米至8米的大幅壁画,他们是从兰州武威张掖酒泉乘大卡车,从酒泉换骡车到安西(瓜州),从安西乘木轮牛车三天三夜到敦煌。赵望云、关山月、李小平、张振铎、杨乡生及黄胄等也是沿着河西走廊、敦煌一带做了较深入的写生与考察。画家韩乐然则是在新疆、敦煌两地写生,两次赴敦煌临摹,并在新疆克孜尔石窟考察,现在中国美术馆收藏有他的150多件作品。吴作人在青海、甘肃、四川北部等地写生,产生了一批有影响的作品、董希文、司徒乔在20世纪40年代进入新疆,董希文以长达三个月的旅程到达敦煌临摹写生,他对壁画有较深入的研究,也善于将壁画艺术溶入自己的创作中。此外,还有徐悲鸿、王临乙、林风眠、李有行、叶浅予、傅抱石、黎雄才、刘勃舒、金维诺、吕斯百、陈之佛、刘开渠、常沙娜等,都有远行敦煌的历程,他们中的一些人甚至不厌其烦的“行行复行行”, 行而返、返而行,这种面向敦煌西行的步伐波及出艺术界,延续到世纪末。“本土西行”成为“中国现代艺术史上的一次‘壮举’。”
“本土西行”不是游山玩水,而是带有强烈的守护民族文化尊严的心理诉求,这种“朝圣”的价值与今天的观光是两种不同本质的行为。今天,莫高窟的“朝圣者”更加络绎不绝,据统计,2015年115万人次,2016年130万人次,今年可能160万人次。当然,“到此一游”式的“朝圣”已变得轻而易举。但条件的变化,更让我们不能忘怀此前朝圣者们筚路蓝缕、风餐露宿、艰辛备尝的日子,这里不必再用更多的词藻来说明敦煌对于一个学习民族文化、探索华夏文明追寻者的价值和意义了。
相对于“本土西行”的远征历程,由一大批文化学者、艺术家所呼吁建立的“敦煌学院”或“敦煌艺术学院”也是另一种形式的“远征”。从陈寅恪“吾国学术之伤心史”开始,我们一直有一种保护、维系、延续敦煌文脉的强烈愿望。因此,于右任先生早就指出:莫高窟的破败不堪“实为可惜”!他说:“这片东方民族艺术之文艺渊海”,如再不保护就是“民族最大之损失”。他最早提议建立“敦煌艺术学院”,“招收大学学艺术学生,就地研习,寓保管于研究之中”。但因为各种原因,20世纪40年代成立的“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并没有招收学生。即使这样,研究所所长常书鸿等一批艺术家仍多次试图建立一所学院,他们认为:中国艺术过于受西方教育影响,忽视了中华民族传统之创造精神,在莫高窟这样一个世界唯一保存完整、规模宏伟的美术馆里,完全可以建立一个很好的美术学院,来培养“有民族精神之现代艺术家”,让更多的朝圣者能在“艺术辉煌史迹之环境中做艺术进修”。常书鸿、段文杰先生还设计、规划在敦煌设立“边疆民族文化学院”、“敦煌艺术研修学院”等方案,敦煌研究院的老师们也都一直在不遗余力的推广敦煌艺术,常书鸿先生亲赴兰州艺术学院任教授课,举办敦煌艺术展览,教授学生学习敦煌艺术。20世纪80年代初期,西北师范大学美术系陈兴华、洪毅然等教授曾提出在兰州建立一所的“敦煌艺术学院”。之后,在兰州、酒泉等地都进行过同样的尝试,西北师范大学较早建立了“敦煌学研究所”,开展敦煌历史的研究与教学。西北师范大学还在1999年至2004年间将音乐、美术专业合并,设立了“敦煌艺术学院”,并建有常书鸿艺术工作室和敦煌艺术研究中心,开展了相关研究。可以说,从上个世纪40年代起,试图在敦煌建立了一个大学的行动从来没有停止过。也许正是前前后后这些机缘的促动,西北师范大学与敦煌市政府2014年共同建立了敦煌的第一所大学二级学院——敦煌学院,时任省委宣传部长的连辑感慨道:“敦煌从此后结束了没有大学的历史!”
为什么人们要孜孜不倦在敦煌设立一所大学,究其原因无外乎莫高窟的存在。“在这里,一粒沙可以窥见一个世界,一朵花中可以欣赏一个天国,敦煌艺术是华夏民族美学的至高境界。”宗白华先生曾惊叹道:“在西陲敦煌洞窟里,竟替我们保留了那千年艺术的灿烂遗影,那些美丽绝伦的人物雕刻,我们的艺术史可以重写了!我们如梦初醒,发现先民的伟力、热力、想象力。”
回顾历史,是为了更好的启示未来,也借此来强调敦煌学子所担负的学习敦煌文化、传承敦煌文化的压力和责任。在敦煌学习,就是为了从这里“获得深厚的启发,鼓舞创造的热情,”就是为了追寻华夏民族的“伟大、热力和想象力。”
做为一名教师,在各位新同学步入校门之际,还要再说几句话:远道西行的你们,不要辜负这次人生难得的敦煌之旅。要在敦煌学有所成,我认为应该练就三心二力,三心是指保持明净心、进取心和欢喜心,二力是指培养定力和能力。
明净而见性,立德而树人,心性与品德本来就是紧密相连的。大学期间是认知世界、体验社会的重要时机,走进校园、走向社会,需要有正确的价值判断和人生目标。明净之心能让我们保持纯正的品质和追求真理的觉悟。
进取搏击、刻苦努力、保持一种最佳的前进步履,不断探索,追索思辨,才能把自己锤炼成有专业水平,有丰富的内涵,有高尚追求的人。
要欢喜这次敦煌的结缘,以微笑对待挫折和失败、以自信面对各种挑战和压力,让你的生活充满活力。
在今天这样一个信息时代,大学也充塞着各种变幻好玩的场景,要专心致志做好一件事情、几件事,都需要定力和能力。培养和提升各种能力,同时又严格自律,不忘初心,不忘学习,需要练就铁一般的定力。我建议同学们从手机屏幕里走出来,融入到书本后的大世界里去,从消极的朋友圈里走出来,融入到现实对话与真实的生活中去。以你的三心两力走近敦煌,走进敦煌,融入敦煌。
作为一名教师,最欣慰的莫过于看到自己的学生长大成人,获得进步。当我在莫高窟看到讲解员中有我们学生;当我在文博会场上,看到志愿者中有我们的学生;当我在美术展厅里以及大剧院的舞台上,看到也有我们的学生时,我的内心充满了自豪感和成就感。东汉学者应劭说:“敦,大也,煌,盛也”;唐代李吉甫也说:“敦煌,以其广开西域,故以盛名。”大而盛,是敦煌的内涵。敦煌之大,不光是指地阔天高,还有追求大、情怀大、心境大。敦煌,有永远看不完、学不完的东西。敦煌,有讲不完的故事,道不尽的情怀。在敦煌看山、看水、看天、看地、乃至看洞子(观摩石窟),都是在诵读历史、穿越时空。走近敦煌,你会觉得神圣而神秘;走进敦煌,你会涌现虔诚和景仰;走过敦煌,你会汲取精神和艺术。敦煌,是人类文化的结晶和瑰宝,是人类过去和未来连接的通道,是人类共同珍藏的大同理想和善与美的典范。敦煌正在改变我们,也即将改变你们。因此,各位新同学要珍惜在敦煌的时光,尽快和敦煌结缘,认真学习敦煌文化,传承华夏传统,创新古老文明。要做敦煌文化的传承者、传播者和创造者。
在敦煌办学,具有的意义是深远的。但因为敦煌的自然与地理条件所限,也因为对敦煌办学有各种不同的理解,建设一所敦煌的大学或几所大学的过程,仍然在路上。虽然敦煌学院的建设已有三年,也远未达到理想的境地,更没有达到前辈大家所期望的那种美好愿景。敦煌学院的建设还需要大家继续协同合作,共谋发展。我也希望老师们、同学们一起发扬学院倡导的莫高精神、大漠精神、戈壁精神和红柳精神,守望敦煌,传承创造,追寻大美,为更好的明天而努力!
再次感谢各位领导嘉宾、各位老师的到来,祝各位新同学学习生活愉快!谢谢!
今天,又是一个欢喜的日子!我们正式迎来了敦煌学院2017级105名新同学。首先,我代表西北师范大学敦煌学院全体师生向新同学的到来表示热烈的欢迎和祝贺!
今年105名新同学有男生40人,女生65人。少数民族中有2名藏族同学,也有从山西、山东招收的10 名学生,省内的学生来自兰州、平凉、定西、庆阳、武威、陇南、张掖、甘南、以及酒泉、嘉峪关等地市,敦煌本地学生1名。现在,敦煌学院共有448名同学在学院就读。
105名新同学的加盟,标志着敦煌学院顺利完成了前后四届学生的招生任务,学院本科教学建制有了一个圆满的结果。
2014年6月28日,敦煌学院挂牌成立,2014年9月教师节的时候,我院为首届大学生举行了开学典礼。现在,敦煌学院已进入办学的第四个年头。当然,对于每年的新同学来说,重要的不是学院在哪里,而是敦煌在哪里,当你选择“敦煌就读”时,最大的疑虑或最大的期盼,我想就是“敦煌”这两个字。
因此,我也要从“敦煌”说起。敦煌,是丝绸之路的重镇,历史文化名城。这里有无数的传说,尘封千年的壁画,还有神奇的鸣沙月泉……。最重要的是,这里吸引了一批又一批朝圣者,敦煌被称为朝圣者的敦煌。一代代朝圣者续写了敦煌的历史,一代代朝圣者也让敦煌走向了世界。这些朝圣者以坚定的、宗教徒般的步伐,经过几年、半年,或三个月时间,到达这个流沙中的绿洲。历史告诉我们:在规模化的朝圣之前,西北有过令人痛心的经历。从19世纪中叶以后,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使得清政府开始允许外国人进入中国内地。一大批外国“探险者”开始涌入,英国人、法国人、俄国人都进入了中国新疆,掠走了大量文物,尤其是瑞典人斯文•赫定从1890年开始三次考察,发现了著名的楼兰古城。最后,在我们主动出击下,他资助的“西北科学考察团”历时八年发现了居延汉简、准噶尔盆地、恐龙化石、高昌遗址以及其它自然科学方面的成果。
也因此,在藏经洞被发现以后,西方人可以轻车熟路、轻而易举地取道敦煌来掠夺文物,中国西北的文化价值在敦煌藏经洞被发现之前,就已经赤裸裸地暴露在别人的眼皮下。斯坦因、伯希和等人掠走的敦煌写经,迅速在西方学界引起了巨大影响,由此诞生了“敦煌学”这门国际显学。直到1930年前后,中国政府以教育部长蔡元培为首的“古物保护委员会”成立,才真正有效的阻止盗宝者的所谓“探险”。在此之后,从官方到民间,从文化学者到艺术家,开始了自己的“朝圣之旅”,引发了“本土西行”这样一个历史事件。
从今天来看,“本土西行”的作用和功效并不亚于去异域求学的“海外西行”。 我不知道同学们是怎样来敦煌的,但绝不会步行而来。但是在当时,偏远的西北交通条件非常艰苦,去西北需要有一定的胆识、方法和毅力,比如,他们多是搭乘当时被称为“羊毛车”的二手苏联大卡车从兰州出发或找机会蹭车,比如吴作人搭乘李约瑟的车子从酒泉去敦煌,韩乐然是搭乘路易·艾黎的捐赠车西行,很多地方是坐马车、毛驴车、牛车、载货车、工程验收车甚至步行。他们想尽各种办法,走向西北,绝不退缩。李丁陇约带领13名学生沿玄奘之路西行,中途12名学生放弃,只有一个敦煌的学生叫刘方跟随他,他后来在兰州、西安、上海、成都、重庆等地举办敦煌“敦煌壁画临摹展”,引起人们对敦煌的关注,他的行动引发了张大千以及常书鸿、韩乐然等一批艺术家的西行。张大千与儿子张心智,女婿萧建初以及孙宗慰等从成都经兰州至敦煌,在敦煌莫高窟、榆林窟临摹200余件壁画,张大千说:如果不是喜欢,来了也会走!他一待就是两年多,舍不得走。孙宗慰经过重庆、成都、西安、兰州沿河西走廊写生,创作有油画、水彩、国画、速写等。王子云1940年率民国政府教育部“西北艺术文物考察团”一行沿途考察,所谓“一行”,最后到达莫高窟的实际只有两、三人,就是王子云、雷震、邹道云,人虽少,但临摹不小,有长6米至8米的大幅壁画,他们是从兰州武威张掖酒泉乘大卡车,从酒泉换骡车到安西(瓜州),从安西乘木轮牛车三天三夜到敦煌。赵望云、关山月、李小平、张振铎、杨乡生及黄胄等也是沿着河西走廊、敦煌一带做了较深入的写生与考察。画家韩乐然则是在新疆、敦煌两地写生,两次赴敦煌临摹,并在新疆克孜尔石窟考察,现在中国美术馆收藏有他的150多件作品。吴作人在青海、甘肃、四川北部等地写生,产生了一批有影响的作品、董希文、司徒乔在20世纪40年代进入新疆,董希文以长达三个月的旅程到达敦煌临摹写生,他对壁画有较深入的研究,也善于将壁画艺术溶入自己的创作中。此外,还有徐悲鸿、王临乙、林风眠、李有行、叶浅予、傅抱石、黎雄才、刘勃舒、金维诺、吕斯百、陈之佛、刘开渠、常沙娜等,都有远行敦煌的历程,他们中的一些人甚至不厌其烦的“行行复行行”, 行而返、返而行,这种面向敦煌西行的步伐波及出艺术界,延续到世纪末。“本土西行”成为“中国现代艺术史上的一次‘壮举’。”
“本土西行”不是游山玩水,而是带有强烈的守护民族文化尊严的心理诉求,这种“朝圣”的价值与今天的观光是两种不同本质的行为。今天,莫高窟的“朝圣者”更加络绎不绝,据统计,2015年115万人次,2016年130万人次,今年可能160万人次。当然,“到此一游”式的“朝圣”已变得轻而易举。但条件的变化,更让我们不能忘怀此前朝圣者们筚路蓝缕、风餐露宿、艰辛备尝的日子,这里不必再用更多的词藻来说明敦煌对于一个学习民族文化、探索华夏文明追寻者的价值和意义了。
相对于“本土西行”的远征历程,由一大批文化学者、艺术家所呼吁建立的“敦煌学院”或“敦煌艺术学院”也是另一种形式的“远征”。从陈寅恪“吾国学术之伤心史”开始,我们一直有一种保护、维系、延续敦煌文脉的强烈愿望。因此,于右任先生早就指出:莫高窟的破败不堪“实为可惜”!他说:“这片东方民族艺术之文艺渊海”,如再不保护就是“民族最大之损失”。他最早提议建立“敦煌艺术学院”,“招收大学学艺术学生,就地研习,寓保管于研究之中”。但因为各种原因,20世纪40年代成立的“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并没有招收学生。即使这样,研究所所长常书鸿等一批艺术家仍多次试图建立一所学院,他们认为:中国艺术过于受西方教育影响,忽视了中华民族传统之创造精神,在莫高窟这样一个世界唯一保存完整、规模宏伟的美术馆里,完全可以建立一个很好的美术学院,来培养“有民族精神之现代艺术家”,让更多的朝圣者能在“艺术辉煌史迹之环境中做艺术进修”。常书鸿、段文杰先生还设计、规划在敦煌设立“边疆民族文化学院”、“敦煌艺术研修学院”等方案,敦煌研究院的老师们也都一直在不遗余力的推广敦煌艺术,常书鸿先生亲赴兰州艺术学院任教授课,举办敦煌艺术展览,教授学生学习敦煌艺术。20世纪80年代初期,西北师范大学美术系陈兴华、洪毅然等教授曾提出在兰州建立一所的“敦煌艺术学院”。之后,在兰州、酒泉等地都进行过同样的尝试,西北师范大学较早建立了“敦煌学研究所”,开展敦煌历史的研究与教学。西北师范大学还在1999年至2004年间将音乐、美术专业合并,设立了“敦煌艺术学院”,并建有常书鸿艺术工作室和敦煌艺术研究中心,开展了相关研究。可以说,从上个世纪40年代起,试图在敦煌建立了一个大学的行动从来没有停止过。也许正是前前后后这些机缘的促动,西北师范大学与敦煌市政府2014年共同建立了敦煌的第一所大学二级学院——敦煌学院,时任省委宣传部长的连辑感慨道:“敦煌从此后结束了没有大学的历史!”
为什么人们要孜孜不倦在敦煌设立一所大学,究其原因无外乎莫高窟的存在。“在这里,一粒沙可以窥见一个世界,一朵花中可以欣赏一个天国,敦煌艺术是华夏民族美学的至高境界。”宗白华先生曾惊叹道:“在西陲敦煌洞窟里,竟替我们保留了那千年艺术的灿烂遗影,那些美丽绝伦的人物雕刻,我们的艺术史可以重写了!我们如梦初醒,发现先民的伟力、热力、想象力。”
回顾历史,是为了更好的启示未来,也借此来强调敦煌学子所担负的学习敦煌文化、传承敦煌文化的压力和责任。在敦煌学习,就是为了从这里“获得深厚的启发,鼓舞创造的热情,”就是为了追寻华夏民族的“伟大、热力和想象力。”
做为一名教师,在各位新同学步入校门之际,还要再说几句话:远道西行的你们,不要辜负这次人生难得的敦煌之旅。要在敦煌学有所成,我认为应该练就三心二力,三心是指保持明净心、进取心和欢喜心,二力是指培养定力和能力。
明净而见性,立德而树人,心性与品德本来就是紧密相连的。大学期间是认知世界、体验社会的重要时机,走进校园、走向社会,需要有正确的价值判断和人生目标。明净之心能让我们保持纯正的品质和追求真理的觉悟。
进取搏击、刻苦努力、保持一种最佳的前进步履,不断探索,追索思辨,才能把自己锤炼成有专业水平,有丰富的内涵,有高尚追求的人。
要欢喜这次敦煌的结缘,以微笑对待挫折和失败、以自信面对各种挑战和压力,让你的生活充满活力。
在今天这样一个信息时代,大学也充塞着各种变幻好玩的场景,要专心致志做好一件事情、几件事,都需要定力和能力。培养和提升各种能力,同时又严格自律,不忘初心,不忘学习,需要练就铁一般的定力。我建议同学们从手机屏幕里走出来,融入到书本后的大世界里去,从消极的朋友圈里走出来,融入到现实对话与真实的生活中去。以你的三心两力走近敦煌,走进敦煌,融入敦煌。
作为一名教师,最欣慰的莫过于看到自己的学生长大成人,获得进步。当我在莫高窟看到讲解员中有我们学生;当我在文博会场上,看到志愿者中有我们的学生;当我在美术展厅里以及大剧院的舞台上,看到也有我们的学生时,我的内心充满了自豪感和成就感。东汉学者应劭说:“敦,大也,煌,盛也”;唐代李吉甫也说:“敦煌,以其广开西域,故以盛名。”大而盛,是敦煌的内涵。敦煌之大,不光是指地阔天高,还有追求大、情怀大、心境大。敦煌,有永远看不完、学不完的东西。敦煌,有讲不完的故事,道不尽的情怀。在敦煌看山、看水、看天、看地、乃至看洞子(观摩石窟),都是在诵读历史、穿越时空。走近敦煌,你会觉得神圣而神秘;走进敦煌,你会涌现虔诚和景仰;走过敦煌,你会汲取精神和艺术。敦煌,是人类文化的结晶和瑰宝,是人类过去和未来连接的通道,是人类共同珍藏的大同理想和善与美的典范。敦煌正在改变我们,也即将改变你们。因此,各位新同学要珍惜在敦煌的时光,尽快和敦煌结缘,认真学习敦煌文化,传承华夏传统,创新古老文明。要做敦煌文化的传承者、传播者和创造者。
在敦煌办学,具有的意义是深远的。但因为敦煌的自然与地理条件所限,也因为对敦煌办学有各种不同的理解,建设一所敦煌的大学或几所大学的过程,仍然在路上。虽然敦煌学院的建设已有三年,也远未达到理想的境地,更没有达到前辈大家所期望的那种美好愿景。敦煌学院的建设还需要大家继续协同合作,共谋发展。我也希望老师们、同学们一起发扬学院倡导的莫高精神、大漠精神、戈壁精神和红柳精神,守望敦煌,传承创造,追寻大美,为更好的明天而努力!
再次感谢各位领导嘉宾、各位老师的到来,祝各位新同学学习生活愉快!谢谢!
上一篇:下一篇: